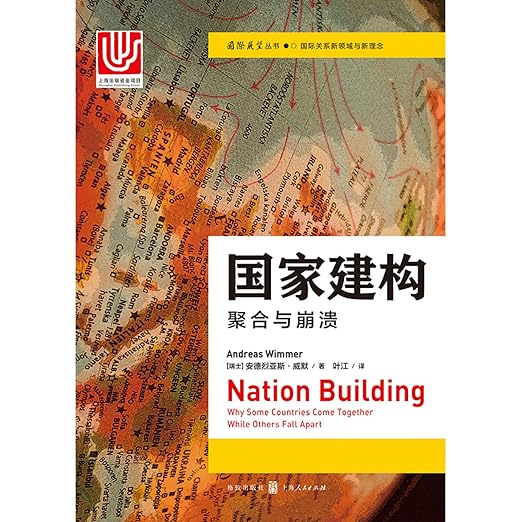原文发表于“政文观止”公众号,2020年4月。
如今占据政治社会学主流的无疑是微观分析和定量方法,而在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中,“将国家拉回理论视野”的吁求早已持续了多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教授是著名的历史社会学者,也是一位逆流而上、建树颇丰的人。试图将上述两个领域中的主流方法放在一个研究中,证明一个重要的“大”话题,显然是他十余年以来的主要工作。2018年拿到巴林顿·摩尔奖的这本《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是其学术道路上的最新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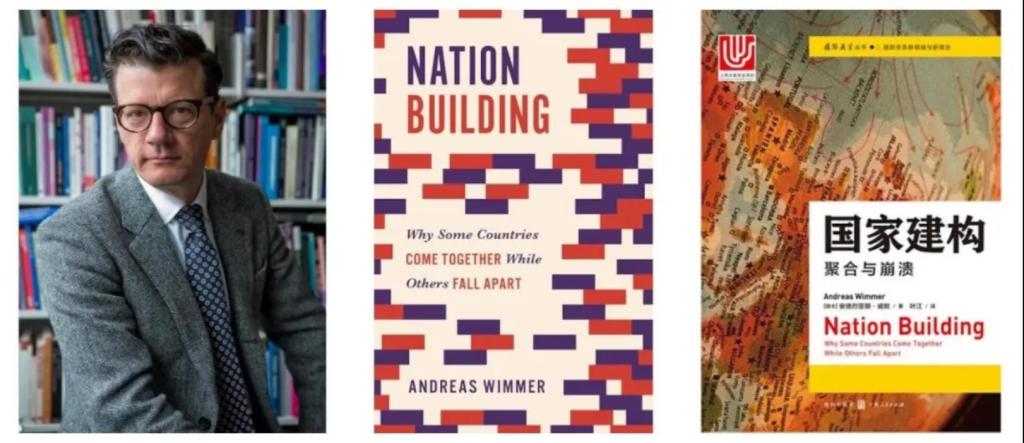
威默教授和获奖著作
对于我这样的后辈政治学人来说,阅读威默最大的收获在于其视野和方法集纳的广阔性。这本书叩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民族怎样聚合成多种多样的国家形式。这既是一个比较政治学的经典命题,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关怀,尤其是近年来全球政治波谲云诡、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暗流涌动,此时再去回望一些重大的根本命题,显然是极为必要且迫切的。这本书也像是同时也像是一场精彩的方法表演秀。作者通过精当的案例选取、丰富的数据分析和缜密的框架设计,同时游走于质性与定量研究两端。一旦“入坑”,读者似乎很难不受到吸引,跟随作者的思路游走于欧亚非诸国,追寻世代更替的长期进程中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那些隐秘线索。
威默的逻辑其实是从常识出发。今日民族国家的形成,归根结底是更小规模的政治联盟聚散发展出来的样态,是不同层级上人和组织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这部作品的核心命题,即国家形成前后,长期的社会进程对其建构来说至关重要。威默在早几年的文章和专著(Wimmer, 2014)中,早已涉及到交换理论和认同理论研究,同行也有相关著述(Mylonas, 2012)。所以本就可以想见,在结合既往成果的基础上,威默一定会以定量和定性两种路数齐头并进。毕竟在《战争之浪》(Waves of War, 2013)里他就已经试着用精确方法挑战对宏观进程的解释。同时,他又从已有的研究出发,以三对不同的国家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三个关键变量:民族国家形成之初的精英政治网络范围(瑞士/比利时);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博茨瓦纳/索马里);书写和文字的同质性对消弭沟通障碍的影响(中国/俄罗斯)。
说到本书的重要亮点,我认为正是这三个变量相关案例比较的选择。六个国家横跨非殖民、后殖民、前殖民三个不同阶段,以及欧非亚三个地区。在大体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威默依赖二手材料(比如中国相关的讨论,基本来自美国的汉学家)编织出较为精细的比较研究,在每个分论点下一正一反来论证其重要性以及成立逻辑:瑞士政治精英形成了与人口构成相当的志愿共同体,而比利时受到了干扰未能形成;博茨瓦纳殖民时期宗主国予以当地政府一定的自决,所以公共物品的提供相对较为合理,而索马里则一切以宗主国为重心,导致氏族政治严重倾斜,结局迥异;中国虽然“十里不同音”,却因为有着统一的文字和科举使得广袤疆域内形成了汉族认同的主体,而俄罗斯书写文字的异质性却使得境内族群之间隔阂较深,影响了国家建构。
上述三条实际上汇集成一个源自于交换理论的核心指标,即前现代国家时期各地区联盟是松散还是紧密。因为无论是人际网络、公共物品还是语言文字,其关键都是社会成本的下降,使得认同感增加,推进共同体建构。因此,本书第五、六章看似是在更广的世界图景内展示定量成果、并为前面的案例研究修补某些逻辑疏漏,但其实是从另一个路径,再度对前面三个变量进行合理性与重要性的论证。以其中所使用的数据库来看,威默应该足以骄傲他和同事前期所做的建设工作。
作为中国的政治学人,我对本书的关注显然会集中在第四章、尤其是论述中国政治的部分。威默在本书中大量参考从魏斐德、何炳棣、艾尔曼到商伟等几代域外中国研究学者的著作,然而从研究清代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以语言同质与否来论证国家建构前景,似乎有些隔靴搔痒,没有触及到核心关切。首先,本书草率地引用了“清承明制”,忽略了这个论断指的是清代内地行省的统治范围,而不包括清廷所辖今日中国的西部、北部等广袤的领土。时间纵轴这条线上,中国的国家建构是否能以语言文字乃至科举作为核心变量颇值得商榷。毕竟以统一文字的科举选拔政治精英的方式,也并不涵盖清朝统治的所有地区。而且科举是否作为中华帝国核心社会流动方式的地位有没有受到过挑战——这个故事也不能从明清开始算起,至少也要追溯到元代。仅仅草率地合并明清、也不追溯比较前朝,显然不够有说服力。其次,清代分区域进行多元化治理、却又将认同统一于中央皇权之下,这应该是海内外学界的共识——新/旧清史之争要害并不在此。这恰恰说明,威默在“语言的同质性”论点中选择清代中国对比其他国家语言的异质性,从学理上来说是不合适的。当时的中国,边疆与内地民众的直接联系很有限,不同区域的语言显然并不相同。语言在政治沟通层面的“汇总”不发生在民众中,而基本维系在地方精英、中央机构和皇帝本人身上。最后,威默当然注意到了北部边境的国家认同问题,但他放下了欧美、日本部分学者所力争的“蒙古认同”(即使他也引用了欧立德的观点讨论“汉”的形成之于中国的意义——当然,这个切入点和引用来源也很清奇迂回,毕竟欧立德更专精于内亚研究),却以今时今日来讨论,从内外蒙古文字的分别,倒推出这种民族认同不具备吸引力——今年,蒙古国刚刚宣布放弃西里尔文、重新采用蒙文作为官方文字,这样一来,威默似乎需要修正他的论点,甚至是重写“汉族的形成”这一节。
中国的国家建构叙事,自古就对“大一统”始终有不言自明的认同。换一种眼光,威默的疑问可能确实是国内学人的“灯下黑”:这种“不言自明”是如何形成的?它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的学者都生活在这种“不言自明”中,很难“把它问题化”(第153页)。在域外学界近年的轮番冲击下,当然已经有不少国内历史学者作了“何为中国”的回应,诞生了一批颇有见地的成果。那么政治学者、或者广义的社会科学学者可以做些什么?威默的研究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借鉴:今天国内的学人,也可以与国际同仁一道,采用更精细的方法回到宏大叙事。一来“以史为鉴”,国内学者已经有条件接受质性方法和定量工具的规范训练,可以将一些材料较为丰富完整的领域和时段加以利用,回应、修正甚至挑战过去一些可商榷的理论;二来“以他人为鉴”,利用比较研究的视角,将“灯下黑”点亮,不光要讲好“中国故事”的独特之处,也争取用学界通行语言(方法和理论)呈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借鉴他国的历史经验,让我们道出自己来自何处、世界将去何方。